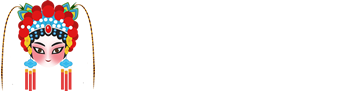陈富年 京剧音乐工作者 陈富年个人简介
陈富年,男,戏曲音乐家。祖籍四川宜宾,生于山东济南。字颐,号希彭,“胡琴圣手”陈彦衡之子。
幼年、青年、中年时期一直在他父亲身边生活,无论是文化知识还是京剧演唱,均由他父亲亲自调教。他随父亲一度客居天津,1909年定居北京,常出入戏院和京剧名角及票友之家,故长期受到京剧艺术的熏陶。陈彦衡常到谭鑫培家切磋技艺和为谭操琴调嗓,陈富年多是随父亲同去谭家,潜移默化地接受了谭腔,并与谭鑫培之子谭小培成为幼年要好的伙伴。1912至1915年余叔岩拜陈彦衡为师学习谭腔,常到陈家学戏和吊嗓,富年则在一侧旁观,耳濡目染,对谭腔逐渐熟悉。余叔岩在陈家学腔中间休息时,常以打把子来舒展肌肉筋骨、恢复疲劳,同时也是避免荒废幼功。富年常跟在叔岩后面模仿比划,日久也熟悉了把子功。在谭鑫培去世的前几年,他经常随父参加堂会和去戏院看谭演出,对谭的演唱达到了痴迷的程度。
陈富年在成年之后,青衣嗓音突然出来了,异常宽亮,他父亲心里很高兴,遂引导培养他学旦角的唱腔。当时陈德霖与陈彦衡常在一起切磋技艺,并请彦衡拉琴调嗓,富年在一旁聆听,逐渐学会了陈德霖的几出拿手戏,如《落花园》、《彩楼配》、《孝义节》等,再上胡琴经过其父的细致匡正后,富年已能熟练演唱。1921年陈彦衡邀请了几位有交情的名角和票友到家中聚会清唱,也安排富年唱了《彩楼配》,有意让众人评论。前来的客人中,丁缉甫唱了《落花园》,余叔岩唱了《洪羊洞》,王君直和舒子元唱了《捉放曹》,陈德霖、恩禹之、张小山唱《坐宫、盗令》,陈的太后、恩的四郎、张的公主,均由陈彦衡操琴,宾主极为尽兴。陈德霖对富年倍加赞赏,使富年和彦衡先生都有了信心,决心深入学习旦角的演唱艺术。当晚天不凑巧下起大雨来,客人只好在陈家客厅内依靠着桌椅打盹,直至黎明雨停后才回家。
王瑶卿“塌中”后,在家编新腔,一些票友老先生对王的新腔颇不以为然,陈彦衡却持不同意见,认为“瑶卿编的新腔虽很特别却是有法度的”,遂派富年到王家一一学会,包括《六月雪》、《玉堂春》、《贺后骂殿》等。富年将学会的新腔及时在父亲跟前哼唱,由陈彦衡全部记录为工尺谱收藏。后来被选为四大坤旦之一的胡碧兰,当时年方十六七岁,已从刘宝云学过旦角的老腔,听说陈富年从王瑶卿那里学了很多新腔,便缠着富年教她,富年只好把刚学会的这些新腔转教给她。“九一八”事变后,受上海票友的邀请,陈氏父子于1931年到上海教戏。已在京、津唱红的胡碧兰陪马连良也来上海演出,对陈富年这位启蒙老师念念不忘,特别邀请他们父子前去给她捧场。陈彦衡看了胡演出的《玉堂春》,夸奖了她的演唱并主动给指教。陈富年听到父亲对胡碧兰的称赞暗暗喜在心里,说明他当年教胡唱王瑶卿的新腔《玉堂春》是成功的,这也是他第一次教戏的经历。
经由在上海的诸多票友介绍,陈彦衡又收了许多学生。陈富年说:“这时我也在东吴大学、中央银行和私人家里教戏。过了一阵,又参加一友人家里小堂会,约我唱《三击掌》,这出戏有一段[西皮原板]的腔很动听,‘昔日里有个孟姜女,她与那范郎送寒衣,哭倒了长城几万里,至今留名在那万古堤’,腔编得好,我最喜爱,父亲也喜欢这段唱,主动为我操琴。因拉与唱配合得如水乳交融,所以演唱博得几次彩声。从此我父对我的唱更有信心,认为可以放心地和我合作了,爷儿俩通力合作的次数也愈来愈多。”
陈富年在上海时结识了俞振飞,他说:“听俞唱出的昆曲声腔,坚如金石,才醒悟自己过去在北京学到的几出昆曲还有相当差距,于是一边教戏一边向俞振飞学昆曲,终于掌握了昆曲发声吐字的基本要领,才算进入昆曲的门槛”。“一二八”事变后,上海住不下去了,恰好四川成都和重庆两地的票友联名请陈彦衡回故乡教戏,陈彦衡欣然接受,但陈富年有教学工作尚未完成,陈彦衡遂随前来迎接的人何欣初和罗孝可于1932年冬先行动身乘船到重庆,陈富年结束教学任务后于次年春也回到重庆与其父相聚。其时,徐碧云正在重庆演出,营业不理想,在各界人士的盛情邀请下,陈彦衡父子接受了与徐碧云合演几场的建议。陈富年演出时就由陈彦衡操琴。富年和徐碧云合演了一出《奇双会》,因为两人的戏路完全相同,均以梅兰芳和程继仙的合作演出为范本,所以丝丝入扣,大获成功。陈氏父子的加盟,扭转了徐碧云在重庆卖座欠佳的局面,虽然涨了票价仍场场爆满,富年也得到可观的酬金用以孝敬父亲,这是陈富年第一次在戏院公开登台演出。
在重庆住了近一年父子二人于1933年秋回到成都,受到成都各界和票友们的热烈欢迎。大家要求两位作示范演出,由陈彦衡操琴、陈富年彩唱,在建成不久专演京剧的春熙大舞台演出了8场,其中3场是募捐戏。演出的戏码和重庆大致相同,包括《宇宙锋》、《二进宫》、《回龙阁》、《奇双会》、《女起解》、《孝义节》、《彩楼配》、《祭塔》,既有陈德霖的拿手戏,也有王瑶卿的新腔戏,演出盛况空前。成都各界的闻人名流纷纷出席观看和捧场,并每场都由四川大学校长王兆荣(宏实)先生登台演说介绍陈彦衡的成就和对全国京剧界的影响。陈富年作为由他父亲一手调教成长的旦角票友,自然也沾光,陈富年的演唱也多次赢得热烈掌声。
陈彦衡回到成都仅100天便因病去世。这种突然的变化给陈富年的生活带来困难,虽然暂时有各票房好友的关照,但终非长久之计。陈富年开始了以教戏为主的忙碌生活。他虽然教旦行和小生戏得心应手,但是成都票房盼他父亲教谭腔的希望便转到他的身上。谭腔他是较为熟悉的,过去听得多却唱得少,但有他父亲的谭腔工尺谱作依据,他便硬着头皮接受下来,同时成都本有几位对谭腔已颇有造诣的票友如罗孝可、杨俪阁、朱戟声和琴票邓干臣等可以互相切磋和请教,他遂在成都多家票房开展了教京戏旦角、小生和老生的活动。他虚心谦和的作风,很快赢得了成都票友们的尊敬。抗战发生后,王蕙芳也来到成都以教戏为生,他的资历声望虽然很高,但精力已不济,故教的学生很少,可以说抗战期间成都的旦角和小生票友几乎都是陈富年的学生。各票房不时在戏院公开演出,都要拉上陈富年为他们把场助威,他是有请必到,成为成都票友活动最活跃的人物之一。他常以陈富年的本名挂牌,但偶尔也用“长歌散人”的化名。据部分不全资料,1935至1937年期间,陈富年以票友身份粉墨登场演出的剧目除前面已提到在1933年演出的外,还有《刺汤》、《古玉杯》、《朱痕记》、《六月雪》、《玉堂春》(饰王金龙)、《群英会》(饰周瑜)等。他偶尔还加演几段学自刘宝全的大鼓,令成都的观众感到很新鲜。
他教的学生不仅仅限于票友,一些专业演员也请他教戏。在20世纪30年代成都春熙大舞台的青年旦角女演员,经过他培养的有蒋艳秋、蒋艳琴、小芙蓉、周慧茹、徐玉凤、蒋金凤等。后来周慧茹不仅在成都,在重庆、昆明、乃至台湾都红过一时,小芙蓉则在雅安和老生孙盛辅搭档成为主要旦角。抗日战争期间,华西坝上有5个大学,除原来的华西外,内迁来了燕京、齐鲁、金陵和金陵女大,学生们成立了京剧社团,也请陈富年教戏,其中一位叫刘孝琼来自北京的学生,学会了《贩马记》,且有创造发挥,演出获得巨大成功,陈富年很满意,而且体会到旧戏只要改革合理,会受到更大欢迎。在票友中他培养出一位小生郑厉如,经陈富年推荐,陪俞振飞1947年在成都演出《群英会》中扮蒋干,《得意缘》中扮二娘,郑的多才多艺得到俞的称赞。此人20世纪40年代末陪董玉苓唱了一段时间,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相继成为成都市京剧团和贵州遵义京剧团的小生主演。这也使陈富年感到欣慰,教戏的心血没有白费。陈富年还参加和辅导成都一个名为“啸隐”昆曲票房的活动,成员几乎都是一些高级知识分子。1947年,俞振飞和他夫人黄曼芸来成都招待各界演出昆曲《太白醉写》、《断桥》,这家昆曲票房都协助演出,陈本人则在俞氏夫妇公开演出的《奇双会》中配演李宝童。
陈富年辅导各票社活动从来不计较条件,不辞辛劳。1959年四川医学院(后称华西医大)京剧队师生合作排演《龙凤呈祥》请他来辅导总响排,来去他都步行,排演在晚上课余时间进行,一直到深夜他都精神抖擞地指导。周肇西饰演的乔玄根据唱片学马连良的腔“劝千岁杀字休出口”,唱完这段[原板转流水]后,他说了一句“就是这样唱的”表示同意,对最后一场《回荆州》的“三插花”走台,他花了较多时间指导。票友们衷心感谢他,但只能在伙食团要了一个大馒头请他吃,票友们觉得很过意不去,他却毫不在乎,边啃馒头边说戏。
成都解放后任新声京剧社编剧,1952年应聘为四川省文联戏曲研究员,1954年任新声京剧社编导组组长。移植、改编及导演的剧目有《钟离春》、《穆桂英》、《屈原》、《蔡文姬》及现代戏《夺印》等。
20世纪50年代初,他在重庆西南军区京剧院任教员。1955年西南大区撤销时,梅兰芳同意安排他去北京,但只能解决他一个人的户口,因而作罢。他回到成都后在成都市京剧团任编导,也给一些青年学员说过戏,并曾在四川音乐学院讲授过几次京剧音乐课。早在1945年他就应成都市社会服务处之邀编写过一出以赛金花为主要人物的京剧《护国花》,为创办平民托儿所募捐,曾由他的学生郑厉如、欧福京等票友在成都昌宜戏院演出,颇为成功,他有了一定的编戏经验。此时他又主持编写了一个剧本《钟离春》,写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故事。1960年成都市京剧团在北京演出,准备上演这个戏,梅兰芳听说后托许姬传打听此剧的编导陈富年的行踪,于是剧团才急电成都叫他速去北京。演出完毕,应邀前来观剧的梅兰芳上台与演员合影,年轻演员都纷纷挤到梅的周围,梅兰芳却不见陈富年,于是问:“陈富年老师在哪儿?”他才从人群中被推出来,梅兰芳急忙拉他到身边,一道与众多演员合影留念。梅是一位很念旧情的人,此后专门请他到家里吃饭,和他畅谈了过去与他父亲陈彦衡切磋技艺的往事。关于这段纪事,在梅所著《舞台生活四十年》第三集中有较详细的记载。
陈富年晚年,集中精力编书、写书。其中《谭鑫培唱腔选集》在他生前已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分成三集出版,由梅兰芳作序,是将他父亲用工尺谱记录的谭鑫培常演的十出戏,与郑隐飞合作,由陈富年照着工尺谱哼唱,郑用简谱记录,并且每出戏陈富年都详加说明表演要点,很有参考学习的价值。夏山楼主说他由于参考了这本书,对谭鑫培在《桑园寄子》中的一句[散板]唱腔才有了把握(参见《吴小如戏曲文录》)。根据他过去在京、津、沪看戏的回忆和体会,他撰文介绍了20世纪早、中期43位京剧生、旦、净著名演员和大鼓演员刘宝全的演唱艺术,其中有26位收入《京剧名家演唱艺术》,他去世后由四川人民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许姬传作序;另外18位京剧演员收入《京剧谈往录》第四编,由北京市政协编辑,北京出版社出版。他除了评价每位演员的艺术成就外,还举出每人的精彩唱腔片段用工尺谱列出加以评论(原稿的工尺谱,出版时由四川音乐学院冯光钰副教授翻译成简谱),说明了他的记忆力惊人。对各种行当演员的评论,除了他自己的见解外,也很可能反映了他父亲的看法。
《回忆录》中有些内容,特别是看戏和评戏的部分,多半已见于上述的三种书,但有些生动的记述则属仅见,比如:“1916年我在北京吉祥戏院,与余叔岩、王君直等一道观看谭鑫培和陈德霖合演的《南天门》,由徐兰沅操琴,陈德霖老夫子在帘内唱倒板‘急急忙忙走得慌’得了满堂彩声。谭出幕后,照常沉着表演,第二句‘点点珠泪洒胸膛’仍是忧郁凄凉的感情。旦唱(第三句):‘鱼儿逃出千层网’,陈在‘网’字上,又翻了一腔,彩声更大。这一下,谭憋不住了,那知他在第四句‘虎口内逃出了两只羊’时(据操琴的徐兰沅说往常他是这样唱的),他不像往常唱‘内’字,而是垫了一个‘哦’字,用炸音高调卯上,由于他嗓音高亢雄健,气势磅礴,声震堂屋,出人意料,使观众突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当时余叔岩也叹息着说‘我不敢这样作,还得悠着点儿才保险!’这可见谭鑫培用腔的功夫。后来陈德霖演《南天门》都只平铺直叙唱过而已,不再卖力要彩,我看的那次也就成了绝唱了。”他在《回忆录》中对旦角重点评论了陈德霖和王瑶卿的高深艺术和对唱腔创新不同的处理方法和见解;对生角则比较了谭鑫培和余叔岩的长短处,他认为谭和余都是顶尖人物,“谭、余都是承先启后的角色,真如天衣无缝”,“谭比余天分高,余叔岩虽天赋不如谭,在小腔方面另创一格,遂成为学谭的第一人”。“余很重视配角的整齐,谭则对配角无特别要求,认为反正观众都是来看我表演的,仗恃自己‘艺高人胆大’,但从整体艺术效果看,则谭的演出不如余那样完美。”
陈富年的著述,除了上述的几种书外,在多种杂志报刊发表的文章有八九十篇,其中有些对京剧名家的评论,与他书中的内容大同小异,也有一些内容和见解独到的文章,一时很难完全收集到,只有留待以后的人继续收集。陈富年署名撰写的《陈彦衡的一生》有多处涉及到他自己的情况。
此外,在20世纪20至30年代他嗓音处于极佳状态时,曾录制了几张唱片,几乎都由他父亲操琴,包括《探寒窑》、《祭江》、《三击掌》、《二进宫》、《落花园》、《庆顶珠》。陈富年在他父亲教导下,不但文墨颇有修养,绘画也达到一定水平,为张大千所赏识,他的某些绘画作品被张大千看中曾纳入张的画展,陈富年自己也举办过画展。陈富年和许姬传的交情也非同一般,两人时常书信往来,交流文字作品。故许姬传对他们父子回到四川直到二人先后去世的情况都了如指掌,反映在许的一些文章中。
陈富年在去世前念念不忘的是,盼望将他的毕生心血体会记录下来以供后来有志于京剧事业的人参考。在《回忆录》中,他曾对承担笔录的朱启明先生说:“请把我一生经历记录下来,公诸于世,以后或许对京剧研究者有所启发,但愿京剧艺术的爱好者能勤学苦练,继续发出永远向前的光辉,则我有生之年,庶几无憾!”
1983年病逝于成都,终年80岁。临终前数月,他因骨折卧病在床期间,请票友朱启明先生笔录下了他口述的《回忆录》,包括他一生听戏、看戏、学戏、唱戏、演戏、教戏、编戏和著书立说评戏的经历和经验体会,希望能传之后世供人参考。
出生:1904年,光绪三十年(甲辰)
逝世:1983年1月25日,农历壬戌年腊月十二日
人物分类
京剧 音乐工作者
幼年、青年、中年时期一直在他父亲身边生活,无论是文化知识还是京剧演唱,均由他父亲亲自调教。他随父亲一度客居天津,1909年定居北京,常出入戏院和京剧名角及票友之家,故长期受到京剧艺术的熏陶。陈彦衡常到谭鑫培家切磋技艺和为谭操琴调嗓,陈富年多是随父亲同去谭家,潜移默化地接受了谭腔,并与谭鑫培之子谭小培成为幼年要好的伙伴。1912至1915年余叔岩拜陈彦衡为师学习谭腔,常到陈家学戏和吊嗓,富年则在一侧旁观,耳濡目染,对谭腔逐渐熟悉。余叔岩在陈家学腔中间休息时,常以打把子来舒展肌肉筋骨、恢复疲劳,同时也是避免荒废幼功。富年常跟在叔岩后面模仿比划,日久也熟悉了把子功。在谭鑫培去世的前几年,他经常随父参加堂会和去戏院看谭演出,对谭的演唱达到了痴迷的程度。
陈富年在成年之后,青衣嗓音突然出来了,异常宽亮,他父亲心里很高兴,遂引导培养他学旦角的唱腔。当时陈德霖与陈彦衡常在一起切磋技艺,并请彦衡拉琴调嗓,富年在一旁聆听,逐渐学会了陈德霖的几出拿手戏,如《落花园》、《彩楼配》、《孝义节》等,再上胡琴经过其父的细致匡正后,富年已能熟练演唱。1921年陈彦衡邀请了几位有交情的名角和票友到家中聚会清唱,也安排富年唱了《彩楼配》,有意让众人评论。前来的客人中,丁缉甫唱了《落花园》,余叔岩唱了《洪羊洞》,王君直和舒子元唱了《捉放曹》,陈德霖、恩禹之、张小山唱《坐宫、盗令》,陈的太后、恩的四郎、张的公主,均由陈彦衡操琴,宾主极为尽兴。陈德霖对富年倍加赞赏,使富年和彦衡先生都有了信心,决心深入学习旦角的演唱艺术。当晚天不凑巧下起大雨来,客人只好在陈家客厅内依靠着桌椅打盹,直至黎明雨停后才回家。
王瑶卿“塌中”后,在家编新腔,一些票友老先生对王的新腔颇不以为然,陈彦衡却持不同意见,认为“瑶卿编的新腔虽很特别却是有法度的”,遂派富年到王家一一学会,包括《六月雪》、《玉堂春》、《贺后骂殿》等。富年将学会的新腔及时在父亲跟前哼唱,由陈彦衡全部记录为工尺谱收藏。后来被选为四大坤旦之一的胡碧兰,当时年方十六七岁,已从刘宝云学过旦角的老腔,听说陈富年从王瑶卿那里学了很多新腔,便缠着富年教她,富年只好把刚学会的这些新腔转教给她。“九一八”事变后,受上海票友的邀请,陈氏父子于1931年到上海教戏。已在京、津唱红的胡碧兰陪马连良也来上海演出,对陈富年这位启蒙老师念念不忘,特别邀请他们父子前去给她捧场。陈彦衡看了胡演出的《玉堂春》,夸奖了她的演唱并主动给指教。陈富年听到父亲对胡碧兰的称赞暗暗喜在心里,说明他当年教胡唱王瑶卿的新腔《玉堂春》是成功的,这也是他第一次教戏的经历。
经由在上海的诸多票友介绍,陈彦衡又收了许多学生。陈富年说:“这时我也在东吴大学、中央银行和私人家里教戏。过了一阵,又参加一友人家里小堂会,约我唱《三击掌》,这出戏有一段[西皮原板]的腔很动听,‘昔日里有个孟姜女,她与那范郎送寒衣,哭倒了长城几万里,至今留名在那万古堤’,腔编得好,我最喜爱,父亲也喜欢这段唱,主动为我操琴。因拉与唱配合得如水乳交融,所以演唱博得几次彩声。从此我父对我的唱更有信心,认为可以放心地和我合作了,爷儿俩通力合作的次数也愈来愈多。”
陈富年在上海时结识了俞振飞,他说:“听俞唱出的昆曲声腔,坚如金石,才醒悟自己过去在北京学到的几出昆曲还有相当差距,于是一边教戏一边向俞振飞学昆曲,终于掌握了昆曲发声吐字的基本要领,才算进入昆曲的门槛”。“一二八”事变后,上海住不下去了,恰好四川成都和重庆两地的票友联名请陈彦衡回故乡教戏,陈彦衡欣然接受,但陈富年有教学工作尚未完成,陈彦衡遂随前来迎接的人何欣初和罗孝可于1932年冬先行动身乘船到重庆,陈富年结束教学任务后于次年春也回到重庆与其父相聚。其时,徐碧云正在重庆演出,营业不理想,在各界人士的盛情邀请下,陈彦衡父子接受了与徐碧云合演几场的建议。陈富年演出时就由陈彦衡操琴。富年和徐碧云合演了一出《奇双会》,因为两人的戏路完全相同,均以梅兰芳和程继仙的合作演出为范本,所以丝丝入扣,大获成功。陈氏父子的加盟,扭转了徐碧云在重庆卖座欠佳的局面,虽然涨了票价仍场场爆满,富年也得到可观的酬金用以孝敬父亲,这是陈富年第一次在戏院公开登台演出。
在重庆住了近一年父子二人于1933年秋回到成都,受到成都各界和票友们的热烈欢迎。大家要求两位作示范演出,由陈彦衡操琴、陈富年彩唱,在建成不久专演京剧的春熙大舞台演出了8场,其中3场是募捐戏。演出的戏码和重庆大致相同,包括《宇宙锋》、《二进宫》、《回龙阁》、《奇双会》、《女起解》、《孝义节》、《彩楼配》、《祭塔》,既有陈德霖的拿手戏,也有王瑶卿的新腔戏,演出盛况空前。成都各界的闻人名流纷纷出席观看和捧场,并每场都由四川大学校长王兆荣(宏实)先生登台演说介绍陈彦衡的成就和对全国京剧界的影响。陈富年作为由他父亲一手调教成长的旦角票友,自然也沾光,陈富年的演唱也多次赢得热烈掌声。
陈彦衡回到成都仅100天便因病去世。这种突然的变化给陈富年的生活带来困难,虽然暂时有各票房好友的关照,但终非长久之计。陈富年开始了以教戏为主的忙碌生活。他虽然教旦行和小生戏得心应手,但是成都票房盼他父亲教谭腔的希望便转到他的身上。谭腔他是较为熟悉的,过去听得多却唱得少,但有他父亲的谭腔工尺谱作依据,他便硬着头皮接受下来,同时成都本有几位对谭腔已颇有造诣的票友如罗孝可、杨俪阁、朱戟声和琴票邓干臣等可以互相切磋和请教,他遂在成都多家票房开展了教京戏旦角、小生和老生的活动。他虚心谦和的作风,很快赢得了成都票友们的尊敬。抗战发生后,王蕙芳也来到成都以教戏为生,他的资历声望虽然很高,但精力已不济,故教的学生很少,可以说抗战期间成都的旦角和小生票友几乎都是陈富年的学生。各票房不时在戏院公开演出,都要拉上陈富年为他们把场助威,他是有请必到,成为成都票友活动最活跃的人物之一。他常以陈富年的本名挂牌,但偶尔也用“长歌散人”的化名。据部分不全资料,1935至1937年期间,陈富年以票友身份粉墨登场演出的剧目除前面已提到在1933年演出的外,还有《刺汤》、《古玉杯》、《朱痕记》、《六月雪》、《玉堂春》(饰王金龙)、《群英会》(饰周瑜)等。他偶尔还加演几段学自刘宝全的大鼓,令成都的观众感到很新鲜。
他教的学生不仅仅限于票友,一些专业演员也请他教戏。在20世纪30年代成都春熙大舞台的青年旦角女演员,经过他培养的有蒋艳秋、蒋艳琴、小芙蓉、周慧茹、徐玉凤、蒋金凤等。后来周慧茹不仅在成都,在重庆、昆明、乃至台湾都红过一时,小芙蓉则在雅安和老生孙盛辅搭档成为主要旦角。抗日战争期间,华西坝上有5个大学,除原来的华西外,内迁来了燕京、齐鲁、金陵和金陵女大,学生们成立了京剧社团,也请陈富年教戏,其中一位叫刘孝琼来自北京的学生,学会了《贩马记》,且有创造发挥,演出获得巨大成功,陈富年很满意,而且体会到旧戏只要改革合理,会受到更大欢迎。在票友中他培养出一位小生郑厉如,经陈富年推荐,陪俞振飞1947年在成都演出《群英会》中扮蒋干,《得意缘》中扮二娘,郑的多才多艺得到俞的称赞。此人20世纪40年代末陪董玉苓唱了一段时间,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相继成为成都市京剧团和贵州遵义京剧团的小生主演。这也使陈富年感到欣慰,教戏的心血没有白费。陈富年还参加和辅导成都一个名为“啸隐”昆曲票房的活动,成员几乎都是一些高级知识分子。1947年,俞振飞和他夫人黄曼芸来成都招待各界演出昆曲《太白醉写》、《断桥》,这家昆曲票房都协助演出,陈本人则在俞氏夫妇公开演出的《奇双会》中配演李宝童。
陈富年辅导各票社活动从来不计较条件,不辞辛劳。1959年四川医学院(后称华西医大)京剧队师生合作排演《龙凤呈祥》请他来辅导总响排,来去他都步行,排演在晚上课余时间进行,一直到深夜他都精神抖擞地指导。周肇西饰演的乔玄根据唱片学马连良的腔“劝千岁杀字休出口”,唱完这段[原板转流水]后,他说了一句“就是这样唱的”表示同意,对最后一场《回荆州》的“三插花”走台,他花了较多时间指导。票友们衷心感谢他,但只能在伙食团要了一个大馒头请他吃,票友们觉得很过意不去,他却毫不在乎,边啃馒头边说戏。
成都解放后任新声京剧社编剧,1952年应聘为四川省文联戏曲研究员,1954年任新声京剧社编导组组长。移植、改编及导演的剧目有《钟离春》、《穆桂英》、《屈原》、《蔡文姬》及现代戏《夺印》等。
20世纪50年代初,他在重庆西南军区京剧院任教员。1955年西南大区撤销时,梅兰芳同意安排他去北京,但只能解决他一个人的户口,因而作罢。他回到成都后在成都市京剧团任编导,也给一些青年学员说过戏,并曾在四川音乐学院讲授过几次京剧音乐课。早在1945年他就应成都市社会服务处之邀编写过一出以赛金花为主要人物的京剧《护国花》,为创办平民托儿所募捐,曾由他的学生郑厉如、欧福京等票友在成都昌宜戏院演出,颇为成功,他有了一定的编戏经验。此时他又主持编写了一个剧本《钟离春》,写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故事。1960年成都市京剧团在北京演出,准备上演这个戏,梅兰芳听说后托许姬传打听此剧的编导陈富年的行踪,于是剧团才急电成都叫他速去北京。演出完毕,应邀前来观剧的梅兰芳上台与演员合影,年轻演员都纷纷挤到梅的周围,梅兰芳却不见陈富年,于是问:“陈富年老师在哪儿?”他才从人群中被推出来,梅兰芳急忙拉他到身边,一道与众多演员合影留念。梅是一位很念旧情的人,此后专门请他到家里吃饭,和他畅谈了过去与他父亲陈彦衡切磋技艺的往事。关于这段纪事,在梅所著《舞台生活四十年》第三集中有较详细的记载。
陈富年晚年,集中精力编书、写书。其中《谭鑫培唱腔选集》在他生前已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分成三集出版,由梅兰芳作序,是将他父亲用工尺谱记录的谭鑫培常演的十出戏,与郑隐飞合作,由陈富年照着工尺谱哼唱,郑用简谱记录,并且每出戏陈富年都详加说明表演要点,很有参考学习的价值。夏山楼主说他由于参考了这本书,对谭鑫培在《桑园寄子》中的一句[散板]唱腔才有了把握(参见《吴小如戏曲文录》)。根据他过去在京、津、沪看戏的回忆和体会,他撰文介绍了20世纪早、中期43位京剧生、旦、净著名演员和大鼓演员刘宝全的演唱艺术,其中有26位收入《京剧名家演唱艺术》,他去世后由四川人民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许姬传作序;另外18位京剧演员收入《京剧谈往录》第四编,由北京市政协编辑,北京出版社出版。他除了评价每位演员的艺术成就外,还举出每人的精彩唱腔片段用工尺谱列出加以评论(原稿的工尺谱,出版时由四川音乐学院冯光钰副教授翻译成简谱),说明了他的记忆力惊人。对各种行当演员的评论,除了他自己的见解外,也很可能反映了他父亲的看法。
《回忆录》中有些内容,特别是看戏和评戏的部分,多半已见于上述的三种书,但有些生动的记述则属仅见,比如:“1916年我在北京吉祥戏院,与余叔岩、王君直等一道观看谭鑫培和陈德霖合演的《南天门》,由徐兰沅操琴,陈德霖老夫子在帘内唱倒板‘急急忙忙走得慌’得了满堂彩声。谭出幕后,照常沉着表演,第二句‘点点珠泪洒胸膛’仍是忧郁凄凉的感情。旦唱(第三句):‘鱼儿逃出千层网’,陈在‘网’字上,又翻了一腔,彩声更大。这一下,谭憋不住了,那知他在第四句‘虎口内逃出了两只羊’时(据操琴的徐兰沅说往常他是这样唱的),他不像往常唱‘内’字,而是垫了一个‘哦’字,用炸音高调卯上,由于他嗓音高亢雄健,气势磅礴,声震堂屋,出人意料,使观众突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当时余叔岩也叹息着说‘我不敢这样作,还得悠着点儿才保险!’这可见谭鑫培用腔的功夫。后来陈德霖演《南天门》都只平铺直叙唱过而已,不再卖力要彩,我看的那次也就成了绝唱了。”他在《回忆录》中对旦角重点评论了陈德霖和王瑶卿的高深艺术和对唱腔创新不同的处理方法和见解;对生角则比较了谭鑫培和余叔岩的长短处,他认为谭和余都是顶尖人物,“谭、余都是承先启后的角色,真如天衣无缝”,“谭比余天分高,余叔岩虽天赋不如谭,在小腔方面另创一格,遂成为学谭的第一人”。“余很重视配角的整齐,谭则对配角无特别要求,认为反正观众都是来看我表演的,仗恃自己‘艺高人胆大’,但从整体艺术效果看,则谭的演出不如余那样完美。”
陈富年的著述,除了上述的几种书外,在多种杂志报刊发表的文章有八九十篇,其中有些对京剧名家的评论,与他书中的内容大同小异,也有一些内容和见解独到的文章,一时很难完全收集到,只有留待以后的人继续收集。陈富年署名撰写的《陈彦衡的一生》有多处涉及到他自己的情况。
此外,在20世纪20至30年代他嗓音处于极佳状态时,曾录制了几张唱片,几乎都由他父亲操琴,包括《探寒窑》、《祭江》、《三击掌》、《二进宫》、《落花园》、《庆顶珠》。陈富年在他父亲教导下,不但文墨颇有修养,绘画也达到一定水平,为张大千所赏识,他的某些绘画作品被张大千看中曾纳入张的画展,陈富年自己也举办过画展。陈富年和许姬传的交情也非同一般,两人时常书信往来,交流文字作品。故许姬传对他们父子回到四川直到二人先后去世的情况都了如指掌,反映在许的一些文章中。
陈富年在去世前念念不忘的是,盼望将他的毕生心血体会记录下来以供后来有志于京剧事业的人参考。在《回忆录》中,他曾对承担笔录的朱启明先生说:“请把我一生经历记录下来,公诸于世,以后或许对京剧研究者有所启发,但愿京剧艺术的爱好者能勤学苦练,继续发出永远向前的光辉,则我有生之年,庶几无憾!”
1983年病逝于成都,终年80岁。临终前数月,他因骨折卧病在床期间,请票友朱启明先生笔录下了他口述的《回忆录》,包括他一生听戏、看戏、学戏、唱戏、演戏、教戏、编戏和著书立说评戏的经历和经验体会,希望能传之后世供人参考。
出生:1904年,光绪三十年(甲辰)
逝世:1983年1月25日,农历壬戌年腊月十二日
人物分类
京剧 音乐工作者
声明:内容由网友分享,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侵犯权益请联系我们修改或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