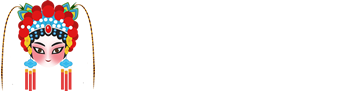谭富英 京剧生行演员 谭富英个人简介
谭富英,男,京剧老生。谱名豫升,小名升格。祖籍湖北江夏(今武昌),生于北京,出身梨园世家。谭鑫培之孙,谭小培之子。
谭富英出生之日,正赶上其父谭小培在中和戏园日场演出大轴《巴骆和》,扮演骆洪勋。按惯例应该早在一个小时前就到后台扮戏候场了,戏园子的大管事指派催戏的“交通”也催过他几次了。眼看着自己的妻子谭德氏就要分娩,他不知道生男生女,似乎不甘心出家门。谭德氏也是梨园家庭出身,其父是清末民初的名小生德珺如。在妻子的劝说下五爷离家赴戏。正要上场时,家里人赶到后台,说:“五爷,祝贺您弄璋之喜。”谭小培一听自己得了儿子,立即眉开眼笑。同事们也纷纷祝贺谭家喜降麒麟。那天的《巴骆和》演得格外精彩,观众一个劲儿地喝彩。所以谭富英的出世,对谭家,尤其对谭小培是一件大喜事。
传到谭富英这代,谭家已经是四代京剧世家。到他六、七岁时,家里就安排老师教他练功学艺。他的开蒙老师是陈秀华。陈会戏多,有丰富的舞台经验,而且教学有方。后来谭富英娶宋继亭的姐姐,而宋母即陈秀华的姐姐,他们就更近了。开始,陈先生每天到谭家教两个小时的课,循序渐进,成果很显著。梨园同行听说老谭请陈秀华给他的孙子说戏了,就都想请其给自己的孩子说戏。一时间,陈秀华身价百倍,学生越来越多,也就没有时间到大外廊营来了,谭富英就只好到陈先生家中学习。经过一年多的时间,一共学了《黄金台》、《文昭关》和《鱼肠剑》三出戏。他的祖父谭鑫培看自己的孙子连唱带比画来了一遍《黄金台》的头场,点点头,抚摸着孙子的头说:“好小子,是这里事。”谭小培忙凑过去问:“老爷子,您看这么学行吗?”老谭反问:“下一步怎么办,总得上场吧,服装道具都好办,场面也好说,可是谁陪他唱,怎么搭班?”小培一听,感到问题不那么简单,知道老爷子要拿主意了,就说:“老爷子,您就吩咐吧。”老谭闭上眼睛,沉默了一会儿,说:“只有一条路,进富连成。砍得怎么也没有旋得圆。不坐科是不行的。”
民国六年,谭富英入了富连成科班。富连成社长叶春善与谭小培订立关书:“立关书人谭小培,长子豫升,现年12岁,情愿加入富连成科班,拜师叶春善,学习梨园生计,言明六年期满。四方生理,任凭师父代行。六年之内所进银钱,归科班收用。无故不准告假回家,确有天灾病孽,各由天命。如私自逃走,两家寻找,年满谢师,但凭天良。日后若有反悔者,由中保人一面承担。空口无凭,立字为据。”科班都应该是七年,所谓“七年大狱”,因为谭富英跟陈秀华学了一年戏,是带艺入科,所以写了六年。
据谭富英说:“我家几代都是科班出身,我父亲是小天仙(小荣椿)的学生,我10岁的时候,我祖父延请陈秀华先生给我开蒙。拜师那天,备了丰盛的酒饭,还约了我外祖父德珺如以及金秀山、陈德霖、张淇林等老先生作陪。秀华先生对先祖说‘我怕教不好。’祖父说‘小孩开蒙只要规规矩矩就得啦。’当我学会了《鱼肠剑》、《黄金台》和半出《昭关》后,祖父见老师一走我就玩去了,觉得在家里学戏太自由,就把叶春善老师请来,当面重托,要把我送进富连成科班。叶老师说:‘我那里是很苦的,怕孩子受不了。’先祖说:‘我们家里都是科班出身,不是少爷,我孙子跟别人家的孩子不能两样,一切奉托。’我初进富连成,叶老师把我安置在萧(长华)老的屋里。一年后,我觉得不合适,就要求搬出来与大家同住一房。我记得,有一天祖父把我叫到他身边,问我在科班学什么戏?我说学《仙圆》,我祖父抚摸着我的头说:‘昆曲扎根最好,你好好用功吧。’他老人家逝世时我才12岁,虽然看过他的戏,但童年初学,印象不深。我学他的艺术,有些是先父和前辈们告诉我的,有些是余(叔岩)老师给我说的。余老师很喜欢我,好像子侄那样亲切,在艺术上是有问必答,知无不言的。”
那时科班对刚入科的学生都偏重武戏和昆曲。因为不管文戏武戏,身段都是很重要的,有了武功基础,对身段帮助极大。在富连成,还有一条,不管唱什么行当,每天一早都得拿顶、下腰、踢腿、劈叉、翻前后桥,以及飞脚、旋子等等,而且都是一天不落,持之以恒。练完武功后,有的调嗓子,有的请先生说戏。唱老生花脸的都得蹬上厚底靴,唱旦角的就得绑上跷,一天都不能脱,只有出门上戏园子演出了,才能脱掉厚底靴,解下跷来。后来谭富英主攻文戏了,一些跟头和武功也就练得少了,但是压腿、踢腿、拿顶、跑圆场还是一点儿也不能少的。
一入科,叶春善先生就让他的哥哥叶福海先生亲自教谭富英学昆腔戏,为的是从嘴里和身段上给他打好基础。给他拍曲并用笛子给他调嗓的是昆曲名家曹心泉。一共学了三出戏,一是《仙圆》,也就是《邯郸梦吕祖度卢生》的一折,谭富英学的是卢生,唱大嗓,但不戴髯口。二是《宁武关》,包括上寿、焚火、别母、乱箭四折,文武并重非常吃功夫,也是科班的必修课。三是《弹词》,即《长生殿》中李龟年弹琵琶卖唱的一段。在昆曲中,这出戏也是比较难的,演出时非常吃力,他每演出一次,就要哑三天嗓子。不过他的爷爷谭鑫培听说孙子学了这三段昆腔戏,非常高兴,认为富连成用昆腔给学生打基础的路子走对了。
在学昆曲的同时,也学一些武生戏,例如《殷家堡》、《落马湖》的黄天霸和《长坂坡》的赵云等等。他第一次登台演出还是老生戏《黄金台》的“巡城搜府”一折。二月入科,闰二月就演出了,在草市精忠庙唱的“行戏”,扮演伊立的花脸是他同科的翟富魁。谭鑫培虽然没有去看他的演出,但是听说谭富英终于将所学的戏演出并得到了舞台锻炼的机会,感到非常欣慰,不久,谭鑫培不幸逝世。
入科不久,谭富英的演出越来越多,大多是富连成总教习萧长华先生亲自给排演的,演出就在前门外的广和楼。有一年夏天,他唱完《珠帘寨》,前胸的痱子都成了大泡,现买痱子粉去擦,整整用了一大包。如果唱《珠帘寨》,总是谭富英唱前部,马连良师兄唱后部。如果由他和马连良合演《群英会·借东风》,就是他演鲁肃,马连良演孔明。
后来,马连良、高百岁等几位唱老生的师兄毕业,谭富英的演出就更多了,几乎天天演戏,《南天门》、《盗宗卷》、《打棍出箱》、《桑园寄子》都唱,不但文武昆乱不挡,而且生行、净行、丑行的角色派什么,就演什么。谭富英入科六年,除了没有贴过片子扮过旦角,连文武小花脸的戏都敢应。后来演大义务戏或者年底演封箱戏《八蜡庙》他反串准演开口跳应工的朱光祖,白口脆爽,每段念白准能赢得满堂彩。萧长华先生当时主要还是让他遵循着老谭的戏路,以唱《碰碑》、《卖马》、《洪羊洞》等戏为主。有一次竟然从头一天的白天一直唱到第二天的天亮,他一个人就唱了五出戏。有时,由他父亲接出来,去应一些堂会戏的演出,使他在舞台上得到充分的锻炼。
一次金鱼胡同的那家花园同仁堂的乐家老太太生日堂会,压轴戏是他和外祖父德珺如、父亲谭小培三代人合演的《四郎探母》,大轴是余叔岩的《珠帘寨》。那天,余三爷一到后台,就冲他们祖孙三代一拱手,说:“厉害呀,你们一家三代都来了,爷仨一块上,德先生,五爷,我给你们道喜啦。”那时谭富英就很有心,前边的戏演完了,也不去玩,到化妆间静静地在一旁看余三爷勾脸。余三爷看谭富英非常文静、老实,很是疼爱,就对他说:“豫升,知道这出戏为什么勾脸吗?”他忙说:“我不知道。”余三爷说:“你坐下,听我告诉你。”他赶紧坐下,余三爷又说:“这出《珠帘寨》原来是一出花脸戏,叫《沙陀国》,是你爷爷把它改成老生戏的,这出戏里很多腔,你琢磨琢磨,都是花脸腔,花脸的扮相就跟徐延昭一样勾老脸,咱们戏班有个规矩,要改什么东西,总得留下点基址,咱们老生不能开脸,就揉脸,勾出纹路就行了,让人一看就知道这出是花脸戏改的。我唱的戏,都是你们谭家的,都是按你爷爷的路子,你爷爷永远是我的法帖。等你出科,就到我那去,我保证有一说一,有二说二,都还给你们谭家。咱们余家和谭家是不分家的,没有比咱们两家更近乎的了,知道吗?”“知道了,谢谢师叔。”那天演出还有一个插曲:举办堂会的乐十爷知道谭小培来了,就到后台看望,一见谭富英如此老成文雅,就对谭小培说:“真是将门虎子,我看令郎大有希望,谭家一定越来越兴旺。”谭小培忙说:“谬奖,谬奖,一个后生晚辈,不要让他太得意了。”乐十爷一手拉过谭富英的手,从自己的手指上褪下一个碧绿晶莹的大扳指,给谭富英戴在手指上,说:“我告诉你,这个扳指是西太后送给你爷爷的,你爷爷又送给我,今天你戴着它上台,希望你好好继承你爷爷的玩意儿。不过今天这个扳指我不能让你带走,我要等你自己挑班的那天,亲自给你送去,这样,你才对得起你爷爷这个扳指。”谭小培一听,知道同仁堂乐家是以信誉闻名于世的,也知道了乐十爷的良苦用心,就对谭富英说:“豫升,这是十爷真心栽培你,还不谢谢十爷。”谭富英马上作揖答谢。13年后谭富英29岁,果然挑班唱戏了,是在开明戏院演唱全部《四郎探母》,乐十爷也果然没有爽约,亲自把那颗扳指送给了谭富英。
谭富英在富连成主要是跟萧长华、雷喜福先生学戏。富连成在教学上有两个最大的特点。一是严格,奉行“打戏”的传统,动辄打通堂。谭富英虽然是谭鑫培的孙子,但也没有因此得到照顾。富连成的第二个特点就是演出多,实践多,学生每天都不离开舞台。由于学生整天泡在剧场里,舞台经验都非常丰富,临场应变,逢场作戏,临时补台,都能应付自如。1922年,谭富英16岁,正是他倒仓(变声)的时候,谭小培开始给谭富英归工归路,正式继承起谭派艺术。在这方面余叔岩先生果不食言,尽心竭力地帮助他从戏路上、演唱规则上纳入谭派的艺术轨道。他在科班学到的许多戏,都经过了余叔岩先生和谭小培的改造、加工。如在富连成的《四郎探母》,谭富英只学到“探母”,而“回令”没有学过,后来是余叔岩先生亲自给他说的“回令”。经过了谭小培和余叔岩一年多的回炉再造,使他艺术上脱胎换骨,具备了搭大班演出的资本。
谭富英出科后第一次正式搭班演出是在王蕙芳的班社。当时班社挂头牌的是徐碧云,老生贯大元,那时谭富英与徐碧云还没有对儿戏,只能在前面演出《捉放曹》、《南阳关》等戏,演出了一个来月后,谭小培感到对儿子没有什么益处,就提出辞班带着儿子到上海搭班去了。谭富英以“谭门本派”的名义在上海三马路的“亦舞台”一亮相,打炮戏是谭派大戏《定军山》,果然一炮而红。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根据“三四二”的合同,实行“四管”,演出三十个夜场,四个星期日又演出了四个白天,最后临别再给老板白白演出二个晚场,作为答谢。一共演出了36场戏,场场满堂,反响热烈。演出一个月后,正赶上上海各剧场“歇伏”,他们父子就到南通去演出了半个月,然后又到苏、杭等地旅游一番,等到立秋,回到上海,到百代唱片公司和大中华唱片公司灌制《定军山》、《南阳关》、《战樊城》、《骂曹》、《斩马谡》、《王佐断臂》、《法门寺》、《战蒲关》和《盗宗卷》等第一批唱片,共16面(8张),以他如此年纪灌制如此数量的唱片,在京剧史上空前绝后。接着,他又在亦舞台与荀慧生合作演出了一个月,同台合作的还有上海的武生白玉昆、花脸王连浦等。有时荀慧生与谭富英合演《法门寺》、《南天门》等戏,有时荀演大轴荀派本戏,谭富英唱压轴戏《战太平》、《打棍出箱》等。有时他也与荀先生编演一些新戏,例如《董其昌三戏杨云友》就是他们合作的热门戏。一个月下来,演出非常圆满,荀慧生也非常满意,所以后来他们在京、津、沪各剧院又多次合作。
尽管上海滩的舆论界一致认为谭富英一出科就能挂头牌,完全可以自己挑班唱戏,可是他的父亲谭小培头脑却非常冷静,他知道,光靠“谭门本派”的招牌,不能掩盖儿子刚出科的稚嫩,拉红票更不是长久之计,必须具备实实在在的艺术资本,才能赢得实实在在的观众群,保持住票房的稳定收入。所以谭小培前思后想,终于做出了稳扎稳打的决定:继续搭班唱戏。从此,谭富英开始了漫长的与“六大名伶”、“四大坤旦”等搭班唱戏的阶段。
谭氏父子从上海回到北京,徐碧云正好要独自挑班“云兴社”,谭富英就在“云兴社”挂二牌。演出《绿珠坠楼》,谭富英的石崇,萧长华的孙秀,尚和玉的司马伦,徐斌寿的潘安。演《八大锤》时,徐碧云的陆文龙,谭富英的王佐,钱金福的金兀术。如果不演出对儿戏,谭富英就在徐碧云的前面演出压轴戏,或与王长林演出《奇冤报》、《天雷报》,或与郝寿臣合演《击鼓骂曹》、《阳平关》等戏。由于王长林、郝寿臣、钱金福等人都曾经受益于谭富英的祖父谭鑫培,所以他们陪谭富英演出都带有奖掖之意和提携之情,加上谭富英的嗓音、扮相、韵味、戏码都极为过硬,而徐碧云又能前演《宇宙锋》后演《八大锤》,或者前演《穆柯寨》后演《汾河湾》双出,具备了与四大名旦分庭抗礼的实力。云兴社这两位年仅20岁左右的后起之秀在北京华乐园可谓名重一时。有一次,谭富英的外祖父德珺如看了外孙的戏特别高兴,就要陪外孙唱一场《群英会》。当然是德珺如的周瑜,谭小培的孔明,谭富英的鲁肃,三代同台。祖孙三代的《群英会》在北京很有号召力,早在张作霖时代,北京宪兵司令王琦为父亲祝寿办堂会,排出最硬的戏码:梅兰芳的《醉酒》,余叔岩的《珠帘寨》和他们祖孙三代的《群英会》,那时谭富英还没有出科。这次演出就在华乐戏园,德珺如已经70多岁了,数年没有登台,为了捧自己的外孙,真是不遗余力。演到“打黄盖”的下场时,老人家掏翎子,抓蟒,抬腿,就已经有些站不稳了,谭富英赶紧上前扶住。谭富英的母亲一看父亲果然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矣,一完戏就忙跑到后台,劝自己的父亲再不要演戏了。从此这位被奉为小生行楷模的前辈就再没有登台唱戏。当时,谭富英每场演出,满分为50块大洋,另外加25块大洋的脑门钱,专为开销鼓师、琴师、跟包和管事等人的小份儿,收入也是比较可观的。
不久,由于徐碧云遭到官司,无法演出,谭富英与尚小云、荀慧生短期合作了一段时间。不久,徐碧云官司了结,前门外大栅栏有名的瑞蚨祥绸缎庄老板孟景侯亲自为他重组“云兴社”,还为他重新翻盖了煤市街的中和园。班社的阵容非常整齐:老生有谭富英、雷喜福和王又宸三位,花脸是郝寿臣和沈福山,小花脸是萧长华,小生是姜妙香和徐斌寿,武生是尚和玉,武旦是朱桂芳。由于云兴社的后台是瑞蚨祥绸缎庄,所以当时的演员都说:“我们搭的是瑞蚨祥的班。”
在云兴社,谭富英与徐碧云合作排演了不少新戏。除与《绿珠坠楼》外,还排演了《虞小翠》、《薛琼英》等。有一出《骊珠梦》,就是全本《游龙戏凤》,在当时具有很高的叫座力。另外一出大受欢迎的戏就是根据《今古奇观》“崔俊臣巧合芙蓉屏”改编的新戏《芙蓉屏》,这出戏由谭富英扮演退隐归林的高纳麟,徐碧云扮演崔夫人,姜妙香扮演崔俊臣。还有一出《挡幽》,本是传统老戏,说的是“烽火戏诸侯”的故事。经过重新整理,增头益尾,也很受欢迎:由萧长华扮演幽王,徐碧云扮演褒姒,谭富英扮演申侯,姜妙香扮演太子。云兴社老戏阵容整齐,新戏场面新鲜,在戏中还增加了一些灯光布景等噱头,例如在《骊珠梦》中就有黄凤冢变色的灯光,在《坠楼》中还有珊瑚的道具用在比富的场面中,这在当时都是新鲜的事情。
1925年,谭富英跟着徐碧云到上海在大兴舞台(上海舞台,也就是后来的天蟾逸夫舞台)演出。就在他们到上海演出第三天的打炮戏时,挑班的徐碧云嗓子哑了,业务立即受到严重的影响。谭富英只好配合当地的演员继续演出了一段时间,挣够了来回的车费,就回到了北京,而云兴社也就报散了。不久,谭富英开始搭尚小云的重庆社,与尚小云先生合作了一年多。接着又到天津的张园游艺场与碧云霞合作了一段时间。碧云霞唱大轴,谭富英在前面唱。三天后,碧云霞不愿意在后面唱,总感觉自己压不住台。但是谭小培认为自己的儿子还不到完全顶大轴的火候,于是停止了合作,回到北京。1928年谭富英继续搭班梅兰芳剧团赴广州、香港演出50余场。
1929年谭富英又参加了万子和的班社,朱琴心为头牌旦角,他是二牌老生,郝寿臣是三牌花脸,在北京鲜鱼口内华乐戏园演出了一两个月。1930年左右,谭富英从朱琴心的戏班退出来,到上海与“四大坤伶”的另一位名角雪艳琴在天蟾舞台合作了一个月。演出后,上海“古代公司”经理郑笺三约请谭富英与雪艳琴联合摄制了他们的第一部电影,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有声电影《四郎探母》,而且第一次骑上真马表演了杨四郎出关的情景,这次拍电影的报酬是7000块大洋。
由沪返京不久,到天津中原公司六楼大剧场开始了自己挑班的实验。一开始起用的旦角是关丽卿,后来换了四大坤旦之一的胡碧兰,唱了两三个月,还排演了《封神榜》、《花灯会》两出新戏。在第一本《封神榜》中,谭富英扮演梅伯,胡碧兰扮演妲己。在第二本中,谭富英扮演商容丞相,搭着棺材上殿死谏,最后撞死在金殿,完全是伍建章骂杨广的路子。《花灯会》演的是柳金蝉的故事,但是只演到柳金蝉被害为止,不带铡判官,也不上包公,是正月十五的应节戏。谭富英扮演柳员外,属于二号人物。胡碧兰唱《玉堂春》,谭富英还配演过蓝袍,都是为了捧胡碧兰。经过一段时间的合作,他们的感情越来越好,胡碧兰想嫁给谭富英,谭富英的原配夫人因病逝世,也有意娶她,但是他的父亲谭小培不同意,因为谭家的规矩就是女人不能唱戏,不能出头露面,这桩好事也就只好作罢了。紧接着,尚小云到天津中原公司演出,也拉着谭富英一起唱了一个短期,然后一起回到北京。就在回北京的火车上,尚先生对谭小培说:“富英跟我的调门差不多,唱着都舒服,这次合作的时间太短了,回北京后我们长期合作一段吧。”这与谭小培的想法不谋而合,他便一口答应,从此谭富英正式搭入尚小云的重庆社,开始了将近两年的合作。
1933年,程砚秋先生从欧洲考察归来,约请谭富英到上海天蟾舞台演出20多天,小生是俞振飞,花脸是金少山。而当时的谭富英就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号召力,所以程砚秋离开上海后,谭富英又被尚小云留在上海,在三星舞台演出了一个月。接着又与梅兰芳在上海黄金影剧院唱了三期。
一年之中,谭富英在上海就先后与四大名旦中的程砚秋、尚小云、梅兰芳三位合作,这就说明已经不再是依附于四大名旦的挎刀演员,而是与四大名旦相得益彰,势均力敌的好角了。为此,许多热心于谭派艺术的人都劝谭小培尽快让谭富英挑班唱戏,被谭小培婉拒。1934年,谭富英回到北京演出几场义务戏后,一过春节就到了汉口的“汉记大舞台”,与梅兰芳合作了半个月,又到武汉的“新市场”与梅兰芳先生合作了十来天。这时要求谭富英自己挑班的呼声更高了,连梅兰芳先生都说:“五爷,我看我们豫升兄弟这台底下的人缘真不错,自己可以独挡一面了,您怎么还不放心呀?”谭小培一听,知道这话是发自肺腑的,连忙拱手致谢:“您抬爱,您的意见我一定会照办的,谢谢您的关照。”看到儿子组班已经是大势所趋,谭小培心中暗暗高兴。
在谭富英与筱翠花先生在北京和天津演出期间,谭小培开始悄悄地斟酌着为儿子组班的事了。1935年下半年,谭小培看到谭富英已经在京、津、沪、汉、鲁各地享有了比较高的声誉,观众群越来越大,足以独自挑班并长期稳定地维持相当的票房收入,古语说:三十而立,这一年谭富英是29岁,如按虚岁正好三十。谭小培找到北京梨园行经励科中的能人陈椿龄,开始正式商议为儿子组班的事情。经过一番磋商,由陈椿龄担任社长,负责约角、经济、联系剧场等事物,因为谭富英乳名为“椿儿”,班社取名“扶椿社”。二牌旦角为王幼卿,三牌武生为周瑞安,铜锤花脸为王泉奎,架子花脸是马连昆,二路老生为哈宝山,丑角是慈瑞泉、慈少泉父子,二旦是许艳芬。根据当时的行情、班社的经济状况,谭富英每演出一场的满分是一百块大洋,他的全堂场面以及两个跟包的,一个箱头上的师傅,一个检场,都算在他的脑门钱中,共计为30块大洋。成班后,谭富英的扶椿社立即在北京的吉祥、华乐、开明、长安、哈尔飞、广德、三庆、中和等各大戏园陆续亮相。正如谭小培的预料,票房收入稳定,观众热情高涨,表演日益娴熟。在北京各戏园子演出了一个周期后,又陆续到天津、汉口、上海等地演出。当然演出的班底也在不断的变化中,仅旦角就先后更换了程玉菁、筱翠花、新艳秋、章遏云、陈丽芳、张君秋、梁小鸾等。
1941年,扶椿社的社长陈椿龄因病辞职,谭小培延请北京“三义永盔头社”的老板韩佩亭担任社长,请乔玉林先生担任大管事,同时启用当年谭鑫培班社的名字“同庆社”为谭富英班社的命名,外出时就学习梅兰芳的方式使用“谭富英剧团”的名义。这就意味着谭富英已经承袭了祖父的艺术衣钵。
就在谭富英37岁那年,他吸上了大烟,心灰意懒,每天再不想练功调嗓,演出《定军山》时,拿起大刀,也感到特别沉重,虽然外界还没有什么反映,但是自己已经感到身体的虚弱和精神的颓废。1946年,他便毅然决定自己一边戒烟,一边加紧练功。他特意请来一位师兄,每天在家中对他监督和陪练,练了八个多月,都没有演出。再演出是为某省的水灾赈灾义演,戏码是《甘露寺》,成绩很不错,从此他就彻底戒除了这个嗜好。
同庆社的名字从1941年起,一直使用到1949年。1944年,韩佩亭社长病故,谭小培又延请华乐戏园经理万子和担任社长。新中国成立后,裘盛戎亲自到大外廊营一号谭宅,以后生晚辈的姿态恳请与谭富英合作。从此谭富英的同庆社与裘盛戎的“戎社”合并,组建了“太平京剧团”。由梁小鸾为三牌旦角、谭富英的妹夫杨盛春为四牌武生、丑角为马富禄。为展示剧团的新面貌,他们首先排演了新戏《将相和》,在上海连续演出了40多场,轰动一时。不久,又到兰州为庆祝“天兰铁路通车典礼”演出了半个多月。回到北京后,根据政府的要求,太平剧团改名为北京京剧二团。1956年,从香港回到北京的马连良组建的马连良剧团又与二团合并,组建了北京京剧团。1957年,又与张君秋的北京京剧三团合并,1960年与赵燕侠的“燕鸣京剧团”合并,组成了北京京剧团。
从与裘盛戎、梁小鸾合作开始,谭富英先生就表现出一位忠厚长者的风范,但又不以长辈的身份压人。裘盛戎先生年轻气盛,在舞台上总有咄咄逼人之势,谭先生从不放在心上,虽然他的嗓音也是宽窄高低运用自如,扮相儒雅俊俏,堪称“最标准的老生奇才”,但是面对比自己晚出道的师侄,总是尽可能地突出对方。在与马连良先生合作时,他又以师弟的姿态,处处谦让,不管排演什么戏,他总是说:“我听师哥的。”总是把大轴戏让给马连良先生。例如马连良先生要与他合作《十道本》,他不会这出戏,完全可以不演,但是他丝毫没有犹豫,马上跟马先生说:“三哥,这出您得教我。”当天就到西单的马宅,毕恭毕敬地请马先生给他说戏。后来排演《赵氏孤儿》,马先生的程婴,谭先生的赵盾,这明明是一个费力不讨好的角色,但是为了增加前半出戏的分量,他主动到马宅,请马先生给他说关外唐韵笙先生演出《闹朝扑犬》的戏路,认真研究“花园”一场的唱腔,把一个不讨好的配角演得有声有色。就是平时走路、开会,他总是谦恭地礼让马先生,人们经常看到,谭先生让马先生先行,马先生请谭先生先行,最后是马先生挽住谭先生的手,并肩而行的感人场面。赵燕侠更是后生晚辈,参加北京京剧团是最晚,最年轻的一个副团长,为了不使她感到新剧团的“欺生”,谭富英甚至在她主演的《辛安驿》前面垫一出中型剧目《摘缨会》。所以说,北京京剧团那么多高级的艺术家在一起合作,却能够互相谦让,彼此和睦,与谭富英先生牺牲自己的名利,以身作则,顾全大局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所以裘盛戎先生在谭富英先生患病时,主动提出与他的师弟谭元寿合演《将相和》;赵燕侠在“文革”后也提出与谭元寿联合搞一个改革实验的剧团。就是在全国京剧名家演出大合作的《赤壁之战》时,他这个“活鲁肃”竟然主动把鲁肃这个角色让给李少春,自己演一个戏份不多的刘备。
谭富英先生是一位大孝子,早出晚归都要到父亲的房间请安,如果外面有饭局,遇到他父亲爱吃的东西,或者是什么新鲜的佳肴,他总是到帐房单交一份钱,请厨房再做一份,饭后用手帕包起来,给父亲送到当面,请父亲品尝。可是当祖国需要他到朝鲜战场慰问志愿军的时候,他的父亲已经卧床不起,病入膏肓了。他每天在床前伺候,却不敢说自己要到朝鲜慰问的事情。因为他明白,他是父亲唯一的儿子,在父亲临终时,父亲最需要的就是他。后来还是谭小培从别人那里知道了儿子即将赴朝的事情,主动对儿子说:“豫升啊,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尽忠不能尽孝,赴朝事大,不能耽搁,不要管我的病,我会好的,你只管去吧。”他这个大孝子听到父亲如此深明大义,感动得泪眼模糊,一再请父亲原谅儿子的不孝。他就这样毅然诀别了弥留之际的父亲踏上了征程。可是列车刚刚开到天津,就接到父亲逝世的噩耗。按谭家的规矩和他自己的心愿,他应该入殓、接三、出殡,大办丧事。可是当领导允许他回家奔丧时,虽然没有提出任何要求,同行们却都认为他这一回北京,是不可能再跨过鸭绿江了。因为按北京的民俗,父亲过世属于大丧事,必须戴重孝,最少也要守孝“五七”,而他,回到北京,哭别了父亲,将遗体刚刚入殓,就戴着热孝日夜兼程赶赴丹东,与慰问团的同志们一同跨过鸭绿江,深入到抗美援朝的前线战壕、掩体中冒着生命危险和零下20度的严寒在冰天雪地的露天广场进行演出活动。
在20世纪50年代末,剧团要到条件相对困难的唐山定期演出,他每次都主动请缨,作为德高望重的老艺术家和年轻人一样去完成最艰苦的演出任务。
正是由于马、谭、张、裘、赵五大头牌精诚合作,技艺超群,北京京剧团连续多年好戏不断,《赵氏孤儿》、《官渡之战》、《状元媒》、《三顾茅庐》等新戏层出不穷。在这些新排剧目中,从表演到唱腔,从音乐到服装、道具,进行了全面改革,使舞台演出焕然一新。不但不要国家负担工资等费用,每年还向国家上缴26万元,这按当年平均工资30元来说,无疑是一笔巨款。
谭富英的嗓音清亮甜脆,吐字行腔不过分雕琢,不追求花哨,用气充实,行腔一气呵成,听来情绪饱满,痛快淋漓,他的演唱被人们称为“新谭派”。因谭在幼年学过武生,故其在武功和身段动作上颇为灵巧、利索。例如他演出的《定军山》一剧,不仅唱工惊人,他那稳练的靠功和刀花动作,干净利落,引入入胜,把一个老当益壮的黄忠形象,演得活龙活现。由于他在艺术上唱做兼能,文武具备,是继马连良之后,成就显著,舞台生涯最长的“四大须生”之一。擅长剧目有《失空斩》、《战太平》、《定军山》、《桑园寄子》、《奇冤报》、《击鼓骂曹》、《洪羊洞》、《搜孤救孤》、《四郎探母》、《桑园会》、《珠帘寨》、《打棍出箱》、《御碑亭》、《群英会》等。
1959年,谭富英先生加入中国共产党。“文革”中,竟被江青等人勒令退党,遭受政治迫害。1977年,“文革”结束,谭富英先生恢复了党籍,落实了政策,本该心情舒畅地重返舞台的时候,他却身染重病,不幸于3月22日逝世。谭富英先生逝世后,北京文艺界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来自全国各地的同行、弟子纷纷赶到北京瞻仰他的遗容,为他献花,为他送行。他的遗体火化后,按国家的最高礼遇,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1924年与宋洁贞(宋继亭之三姐)女士结婚,生育寿颐(元寿)、寿丰(韵寿)、寿永(喜寿)三子,在宋氏生喜寿时因患产后风不幸早逝。1936年谭富英续娶姜志昭(姜妙香之女)女士,生下三女凤云、凤霞、凤珠,一子寿昌。1947年,姜志昭夫人病逝。1948年谭富英续娶杨淑贤女士,生子寿康、小英。子寿颐、寿丰、寿永和寿昌在京剧界分别工文武老生、丑角、武生和场面。

出生:1906年10月15日,光绪三十二年(丙午)八月廿八日
逝世:1977年3月22日,农历丁巳年二月初三日
人物分类
京剧 生行演员
科班院校
富连成社 富字科 学生
谭富英出生之日,正赶上其父谭小培在中和戏园日场演出大轴《巴骆和》,扮演骆洪勋。按惯例应该早在一个小时前就到后台扮戏候场了,戏园子的大管事指派催戏的“交通”也催过他几次了。眼看着自己的妻子谭德氏就要分娩,他不知道生男生女,似乎不甘心出家门。谭德氏也是梨园家庭出身,其父是清末民初的名小生德珺如。在妻子的劝说下五爷离家赴戏。正要上场时,家里人赶到后台,说:“五爷,祝贺您弄璋之喜。”谭小培一听自己得了儿子,立即眉开眼笑。同事们也纷纷祝贺谭家喜降麒麟。那天的《巴骆和》演得格外精彩,观众一个劲儿地喝彩。所以谭富英的出世,对谭家,尤其对谭小培是一件大喜事。
传到谭富英这代,谭家已经是四代京剧世家。到他六、七岁时,家里就安排老师教他练功学艺。他的开蒙老师是陈秀华。陈会戏多,有丰富的舞台经验,而且教学有方。后来谭富英娶宋继亭的姐姐,而宋母即陈秀华的姐姐,他们就更近了。开始,陈先生每天到谭家教两个小时的课,循序渐进,成果很显著。梨园同行听说老谭请陈秀华给他的孙子说戏了,就都想请其给自己的孩子说戏。一时间,陈秀华身价百倍,学生越来越多,也就没有时间到大外廊营来了,谭富英就只好到陈先生家中学习。经过一年多的时间,一共学了《黄金台》、《文昭关》和《鱼肠剑》三出戏。他的祖父谭鑫培看自己的孙子连唱带比画来了一遍《黄金台》的头场,点点头,抚摸着孙子的头说:“好小子,是这里事。”谭小培忙凑过去问:“老爷子,您看这么学行吗?”老谭反问:“下一步怎么办,总得上场吧,服装道具都好办,场面也好说,可是谁陪他唱,怎么搭班?”小培一听,感到问题不那么简单,知道老爷子要拿主意了,就说:“老爷子,您就吩咐吧。”老谭闭上眼睛,沉默了一会儿,说:“只有一条路,进富连成。砍得怎么也没有旋得圆。不坐科是不行的。”
民国六年,谭富英入了富连成科班。富连成社长叶春善与谭小培订立关书:“立关书人谭小培,长子豫升,现年12岁,情愿加入富连成科班,拜师叶春善,学习梨园生计,言明六年期满。四方生理,任凭师父代行。六年之内所进银钱,归科班收用。无故不准告假回家,确有天灾病孽,各由天命。如私自逃走,两家寻找,年满谢师,但凭天良。日后若有反悔者,由中保人一面承担。空口无凭,立字为据。”科班都应该是七年,所谓“七年大狱”,因为谭富英跟陈秀华学了一年戏,是带艺入科,所以写了六年。
据谭富英说:“我家几代都是科班出身,我父亲是小天仙(小荣椿)的学生,我10岁的时候,我祖父延请陈秀华先生给我开蒙。拜师那天,备了丰盛的酒饭,还约了我外祖父德珺如以及金秀山、陈德霖、张淇林等老先生作陪。秀华先生对先祖说‘我怕教不好。’祖父说‘小孩开蒙只要规规矩矩就得啦。’当我学会了《鱼肠剑》、《黄金台》和半出《昭关》后,祖父见老师一走我就玩去了,觉得在家里学戏太自由,就把叶春善老师请来,当面重托,要把我送进富连成科班。叶老师说:‘我那里是很苦的,怕孩子受不了。’先祖说:‘我们家里都是科班出身,不是少爷,我孙子跟别人家的孩子不能两样,一切奉托。’我初进富连成,叶老师把我安置在萧(长华)老的屋里。一年后,我觉得不合适,就要求搬出来与大家同住一房。我记得,有一天祖父把我叫到他身边,问我在科班学什么戏?我说学《仙圆》,我祖父抚摸着我的头说:‘昆曲扎根最好,你好好用功吧。’他老人家逝世时我才12岁,虽然看过他的戏,但童年初学,印象不深。我学他的艺术,有些是先父和前辈们告诉我的,有些是余(叔岩)老师给我说的。余老师很喜欢我,好像子侄那样亲切,在艺术上是有问必答,知无不言的。”
那时科班对刚入科的学生都偏重武戏和昆曲。因为不管文戏武戏,身段都是很重要的,有了武功基础,对身段帮助极大。在富连成,还有一条,不管唱什么行当,每天一早都得拿顶、下腰、踢腿、劈叉、翻前后桥,以及飞脚、旋子等等,而且都是一天不落,持之以恒。练完武功后,有的调嗓子,有的请先生说戏。唱老生花脸的都得蹬上厚底靴,唱旦角的就得绑上跷,一天都不能脱,只有出门上戏园子演出了,才能脱掉厚底靴,解下跷来。后来谭富英主攻文戏了,一些跟头和武功也就练得少了,但是压腿、踢腿、拿顶、跑圆场还是一点儿也不能少的。
一入科,叶春善先生就让他的哥哥叶福海先生亲自教谭富英学昆腔戏,为的是从嘴里和身段上给他打好基础。给他拍曲并用笛子给他调嗓的是昆曲名家曹心泉。一共学了三出戏,一是《仙圆》,也就是《邯郸梦吕祖度卢生》的一折,谭富英学的是卢生,唱大嗓,但不戴髯口。二是《宁武关》,包括上寿、焚火、别母、乱箭四折,文武并重非常吃功夫,也是科班的必修课。三是《弹词》,即《长生殿》中李龟年弹琵琶卖唱的一段。在昆曲中,这出戏也是比较难的,演出时非常吃力,他每演出一次,就要哑三天嗓子。不过他的爷爷谭鑫培听说孙子学了这三段昆腔戏,非常高兴,认为富连成用昆腔给学生打基础的路子走对了。
在学昆曲的同时,也学一些武生戏,例如《殷家堡》、《落马湖》的黄天霸和《长坂坡》的赵云等等。他第一次登台演出还是老生戏《黄金台》的“巡城搜府”一折。二月入科,闰二月就演出了,在草市精忠庙唱的“行戏”,扮演伊立的花脸是他同科的翟富魁。谭鑫培虽然没有去看他的演出,但是听说谭富英终于将所学的戏演出并得到了舞台锻炼的机会,感到非常欣慰,不久,谭鑫培不幸逝世。
入科不久,谭富英的演出越来越多,大多是富连成总教习萧长华先生亲自给排演的,演出就在前门外的广和楼。有一年夏天,他唱完《珠帘寨》,前胸的痱子都成了大泡,现买痱子粉去擦,整整用了一大包。如果唱《珠帘寨》,总是谭富英唱前部,马连良师兄唱后部。如果由他和马连良合演《群英会·借东风》,就是他演鲁肃,马连良演孔明。
后来,马连良、高百岁等几位唱老生的师兄毕业,谭富英的演出就更多了,几乎天天演戏,《南天门》、《盗宗卷》、《打棍出箱》、《桑园寄子》都唱,不但文武昆乱不挡,而且生行、净行、丑行的角色派什么,就演什么。谭富英入科六年,除了没有贴过片子扮过旦角,连文武小花脸的戏都敢应。后来演大义务戏或者年底演封箱戏《八蜡庙》他反串准演开口跳应工的朱光祖,白口脆爽,每段念白准能赢得满堂彩。萧长华先生当时主要还是让他遵循着老谭的戏路,以唱《碰碑》、《卖马》、《洪羊洞》等戏为主。有一次竟然从头一天的白天一直唱到第二天的天亮,他一个人就唱了五出戏。有时,由他父亲接出来,去应一些堂会戏的演出,使他在舞台上得到充分的锻炼。
一次金鱼胡同的那家花园同仁堂的乐家老太太生日堂会,压轴戏是他和外祖父德珺如、父亲谭小培三代人合演的《四郎探母》,大轴是余叔岩的《珠帘寨》。那天,余三爷一到后台,就冲他们祖孙三代一拱手,说:“厉害呀,你们一家三代都来了,爷仨一块上,德先生,五爷,我给你们道喜啦。”那时谭富英就很有心,前边的戏演完了,也不去玩,到化妆间静静地在一旁看余三爷勾脸。余三爷看谭富英非常文静、老实,很是疼爱,就对他说:“豫升,知道这出戏为什么勾脸吗?”他忙说:“我不知道。”余三爷说:“你坐下,听我告诉你。”他赶紧坐下,余三爷又说:“这出《珠帘寨》原来是一出花脸戏,叫《沙陀国》,是你爷爷把它改成老生戏的,这出戏里很多腔,你琢磨琢磨,都是花脸腔,花脸的扮相就跟徐延昭一样勾老脸,咱们戏班有个规矩,要改什么东西,总得留下点基址,咱们老生不能开脸,就揉脸,勾出纹路就行了,让人一看就知道这出是花脸戏改的。我唱的戏,都是你们谭家的,都是按你爷爷的路子,你爷爷永远是我的法帖。等你出科,就到我那去,我保证有一说一,有二说二,都还给你们谭家。咱们余家和谭家是不分家的,没有比咱们两家更近乎的了,知道吗?”“知道了,谢谢师叔。”那天演出还有一个插曲:举办堂会的乐十爷知道谭小培来了,就到后台看望,一见谭富英如此老成文雅,就对谭小培说:“真是将门虎子,我看令郎大有希望,谭家一定越来越兴旺。”谭小培忙说:“谬奖,谬奖,一个后生晚辈,不要让他太得意了。”乐十爷一手拉过谭富英的手,从自己的手指上褪下一个碧绿晶莹的大扳指,给谭富英戴在手指上,说:“我告诉你,这个扳指是西太后送给你爷爷的,你爷爷又送给我,今天你戴着它上台,希望你好好继承你爷爷的玩意儿。不过今天这个扳指我不能让你带走,我要等你自己挑班的那天,亲自给你送去,这样,你才对得起你爷爷这个扳指。”谭小培一听,知道同仁堂乐家是以信誉闻名于世的,也知道了乐十爷的良苦用心,就对谭富英说:“豫升,这是十爷真心栽培你,还不谢谢十爷。”谭富英马上作揖答谢。13年后谭富英29岁,果然挑班唱戏了,是在开明戏院演唱全部《四郎探母》,乐十爷也果然没有爽约,亲自把那颗扳指送给了谭富英。
谭富英在富连成主要是跟萧长华、雷喜福先生学戏。富连成在教学上有两个最大的特点。一是严格,奉行“打戏”的传统,动辄打通堂。谭富英虽然是谭鑫培的孙子,但也没有因此得到照顾。富连成的第二个特点就是演出多,实践多,学生每天都不离开舞台。由于学生整天泡在剧场里,舞台经验都非常丰富,临场应变,逢场作戏,临时补台,都能应付自如。1922年,谭富英16岁,正是他倒仓(变声)的时候,谭小培开始给谭富英归工归路,正式继承起谭派艺术。在这方面余叔岩先生果不食言,尽心竭力地帮助他从戏路上、演唱规则上纳入谭派的艺术轨道。他在科班学到的许多戏,都经过了余叔岩先生和谭小培的改造、加工。如在富连成的《四郎探母》,谭富英只学到“探母”,而“回令”没有学过,后来是余叔岩先生亲自给他说的“回令”。经过了谭小培和余叔岩一年多的回炉再造,使他艺术上脱胎换骨,具备了搭大班演出的资本。
谭富英出科后第一次正式搭班演出是在王蕙芳的班社。当时班社挂头牌的是徐碧云,老生贯大元,那时谭富英与徐碧云还没有对儿戏,只能在前面演出《捉放曹》、《南阳关》等戏,演出了一个来月后,谭小培感到对儿子没有什么益处,就提出辞班带着儿子到上海搭班去了。谭富英以“谭门本派”的名义在上海三马路的“亦舞台”一亮相,打炮戏是谭派大戏《定军山》,果然一炮而红。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根据“三四二”的合同,实行“四管”,演出三十个夜场,四个星期日又演出了四个白天,最后临别再给老板白白演出二个晚场,作为答谢。一共演出了36场戏,场场满堂,反响热烈。演出一个月后,正赶上上海各剧场“歇伏”,他们父子就到南通去演出了半个月,然后又到苏、杭等地旅游一番,等到立秋,回到上海,到百代唱片公司和大中华唱片公司灌制《定军山》、《南阳关》、《战樊城》、《骂曹》、《斩马谡》、《王佐断臂》、《法门寺》、《战蒲关》和《盗宗卷》等第一批唱片,共16面(8张),以他如此年纪灌制如此数量的唱片,在京剧史上空前绝后。接着,他又在亦舞台与荀慧生合作演出了一个月,同台合作的还有上海的武生白玉昆、花脸王连浦等。有时荀慧生与谭富英合演《法门寺》、《南天门》等戏,有时荀演大轴荀派本戏,谭富英唱压轴戏《战太平》、《打棍出箱》等。有时他也与荀先生编演一些新戏,例如《董其昌三戏杨云友》就是他们合作的热门戏。一个月下来,演出非常圆满,荀慧生也非常满意,所以后来他们在京、津、沪各剧院又多次合作。
尽管上海滩的舆论界一致认为谭富英一出科就能挂头牌,完全可以自己挑班唱戏,可是他的父亲谭小培头脑却非常冷静,他知道,光靠“谭门本派”的招牌,不能掩盖儿子刚出科的稚嫩,拉红票更不是长久之计,必须具备实实在在的艺术资本,才能赢得实实在在的观众群,保持住票房的稳定收入。所以谭小培前思后想,终于做出了稳扎稳打的决定:继续搭班唱戏。从此,谭富英开始了漫长的与“六大名伶”、“四大坤旦”等搭班唱戏的阶段。
谭氏父子从上海回到北京,徐碧云正好要独自挑班“云兴社”,谭富英就在“云兴社”挂二牌。演出《绿珠坠楼》,谭富英的石崇,萧长华的孙秀,尚和玉的司马伦,徐斌寿的潘安。演《八大锤》时,徐碧云的陆文龙,谭富英的王佐,钱金福的金兀术。如果不演出对儿戏,谭富英就在徐碧云的前面演出压轴戏,或与王长林演出《奇冤报》、《天雷报》,或与郝寿臣合演《击鼓骂曹》、《阳平关》等戏。由于王长林、郝寿臣、钱金福等人都曾经受益于谭富英的祖父谭鑫培,所以他们陪谭富英演出都带有奖掖之意和提携之情,加上谭富英的嗓音、扮相、韵味、戏码都极为过硬,而徐碧云又能前演《宇宙锋》后演《八大锤》,或者前演《穆柯寨》后演《汾河湾》双出,具备了与四大名旦分庭抗礼的实力。云兴社这两位年仅20岁左右的后起之秀在北京华乐园可谓名重一时。有一次,谭富英的外祖父德珺如看了外孙的戏特别高兴,就要陪外孙唱一场《群英会》。当然是德珺如的周瑜,谭小培的孔明,谭富英的鲁肃,三代同台。祖孙三代的《群英会》在北京很有号召力,早在张作霖时代,北京宪兵司令王琦为父亲祝寿办堂会,排出最硬的戏码:梅兰芳的《醉酒》,余叔岩的《珠帘寨》和他们祖孙三代的《群英会》,那时谭富英还没有出科。这次演出就在华乐戏园,德珺如已经70多岁了,数年没有登台,为了捧自己的外孙,真是不遗余力。演到“打黄盖”的下场时,老人家掏翎子,抓蟒,抬腿,就已经有些站不稳了,谭富英赶紧上前扶住。谭富英的母亲一看父亲果然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矣,一完戏就忙跑到后台,劝自己的父亲再不要演戏了。从此这位被奉为小生行楷模的前辈就再没有登台唱戏。当时,谭富英每场演出,满分为50块大洋,另外加25块大洋的脑门钱,专为开销鼓师、琴师、跟包和管事等人的小份儿,收入也是比较可观的。
不久,由于徐碧云遭到官司,无法演出,谭富英与尚小云、荀慧生短期合作了一段时间。不久,徐碧云官司了结,前门外大栅栏有名的瑞蚨祥绸缎庄老板孟景侯亲自为他重组“云兴社”,还为他重新翻盖了煤市街的中和园。班社的阵容非常整齐:老生有谭富英、雷喜福和王又宸三位,花脸是郝寿臣和沈福山,小花脸是萧长华,小生是姜妙香和徐斌寿,武生是尚和玉,武旦是朱桂芳。由于云兴社的后台是瑞蚨祥绸缎庄,所以当时的演员都说:“我们搭的是瑞蚨祥的班。”
在云兴社,谭富英与徐碧云合作排演了不少新戏。除与《绿珠坠楼》外,还排演了《虞小翠》、《薛琼英》等。有一出《骊珠梦》,就是全本《游龙戏凤》,在当时具有很高的叫座力。另外一出大受欢迎的戏就是根据《今古奇观》“崔俊臣巧合芙蓉屏”改编的新戏《芙蓉屏》,这出戏由谭富英扮演退隐归林的高纳麟,徐碧云扮演崔夫人,姜妙香扮演崔俊臣。还有一出《挡幽》,本是传统老戏,说的是“烽火戏诸侯”的故事。经过重新整理,增头益尾,也很受欢迎:由萧长华扮演幽王,徐碧云扮演褒姒,谭富英扮演申侯,姜妙香扮演太子。云兴社老戏阵容整齐,新戏场面新鲜,在戏中还增加了一些灯光布景等噱头,例如在《骊珠梦》中就有黄凤冢变色的灯光,在《坠楼》中还有珊瑚的道具用在比富的场面中,这在当时都是新鲜的事情。
1925年,谭富英跟着徐碧云到上海在大兴舞台(上海舞台,也就是后来的天蟾逸夫舞台)演出。就在他们到上海演出第三天的打炮戏时,挑班的徐碧云嗓子哑了,业务立即受到严重的影响。谭富英只好配合当地的演员继续演出了一段时间,挣够了来回的车费,就回到了北京,而云兴社也就报散了。不久,谭富英开始搭尚小云的重庆社,与尚小云先生合作了一年多。接着又到天津的张园游艺场与碧云霞合作了一段时间。碧云霞唱大轴,谭富英在前面唱。三天后,碧云霞不愿意在后面唱,总感觉自己压不住台。但是谭小培认为自己的儿子还不到完全顶大轴的火候,于是停止了合作,回到北京。1928年谭富英继续搭班梅兰芳剧团赴广州、香港演出50余场。
1929年谭富英又参加了万子和的班社,朱琴心为头牌旦角,他是二牌老生,郝寿臣是三牌花脸,在北京鲜鱼口内华乐戏园演出了一两个月。1930年左右,谭富英从朱琴心的戏班退出来,到上海与“四大坤伶”的另一位名角雪艳琴在天蟾舞台合作了一个月。演出后,上海“古代公司”经理郑笺三约请谭富英与雪艳琴联合摄制了他们的第一部电影,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有声电影《四郎探母》,而且第一次骑上真马表演了杨四郎出关的情景,这次拍电影的报酬是7000块大洋。
由沪返京不久,到天津中原公司六楼大剧场开始了自己挑班的实验。一开始起用的旦角是关丽卿,后来换了四大坤旦之一的胡碧兰,唱了两三个月,还排演了《封神榜》、《花灯会》两出新戏。在第一本《封神榜》中,谭富英扮演梅伯,胡碧兰扮演妲己。在第二本中,谭富英扮演商容丞相,搭着棺材上殿死谏,最后撞死在金殿,完全是伍建章骂杨广的路子。《花灯会》演的是柳金蝉的故事,但是只演到柳金蝉被害为止,不带铡判官,也不上包公,是正月十五的应节戏。谭富英扮演柳员外,属于二号人物。胡碧兰唱《玉堂春》,谭富英还配演过蓝袍,都是为了捧胡碧兰。经过一段时间的合作,他们的感情越来越好,胡碧兰想嫁给谭富英,谭富英的原配夫人因病逝世,也有意娶她,但是他的父亲谭小培不同意,因为谭家的规矩就是女人不能唱戏,不能出头露面,这桩好事也就只好作罢了。紧接着,尚小云到天津中原公司演出,也拉着谭富英一起唱了一个短期,然后一起回到北京。就在回北京的火车上,尚先生对谭小培说:“富英跟我的调门差不多,唱着都舒服,这次合作的时间太短了,回北京后我们长期合作一段吧。”这与谭小培的想法不谋而合,他便一口答应,从此谭富英正式搭入尚小云的重庆社,开始了将近两年的合作。
1933年,程砚秋先生从欧洲考察归来,约请谭富英到上海天蟾舞台演出20多天,小生是俞振飞,花脸是金少山。而当时的谭富英就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号召力,所以程砚秋离开上海后,谭富英又被尚小云留在上海,在三星舞台演出了一个月。接着又与梅兰芳在上海黄金影剧院唱了三期。
一年之中,谭富英在上海就先后与四大名旦中的程砚秋、尚小云、梅兰芳三位合作,这就说明已经不再是依附于四大名旦的挎刀演员,而是与四大名旦相得益彰,势均力敌的好角了。为此,许多热心于谭派艺术的人都劝谭小培尽快让谭富英挑班唱戏,被谭小培婉拒。1934年,谭富英回到北京演出几场义务戏后,一过春节就到了汉口的“汉记大舞台”,与梅兰芳合作了半个月,又到武汉的“新市场”与梅兰芳先生合作了十来天。这时要求谭富英自己挑班的呼声更高了,连梅兰芳先生都说:“五爷,我看我们豫升兄弟这台底下的人缘真不错,自己可以独挡一面了,您怎么还不放心呀?”谭小培一听,知道这话是发自肺腑的,连忙拱手致谢:“您抬爱,您的意见我一定会照办的,谢谢您的关照。”看到儿子组班已经是大势所趋,谭小培心中暗暗高兴。
在谭富英与筱翠花先生在北京和天津演出期间,谭小培开始悄悄地斟酌着为儿子组班的事了。1935年下半年,谭小培看到谭富英已经在京、津、沪、汉、鲁各地享有了比较高的声誉,观众群越来越大,足以独自挑班并长期稳定地维持相当的票房收入,古语说:三十而立,这一年谭富英是29岁,如按虚岁正好三十。谭小培找到北京梨园行经励科中的能人陈椿龄,开始正式商议为儿子组班的事情。经过一番磋商,由陈椿龄担任社长,负责约角、经济、联系剧场等事物,因为谭富英乳名为“椿儿”,班社取名“扶椿社”。二牌旦角为王幼卿,三牌武生为周瑞安,铜锤花脸为王泉奎,架子花脸是马连昆,二路老生为哈宝山,丑角是慈瑞泉、慈少泉父子,二旦是许艳芬。根据当时的行情、班社的经济状况,谭富英每演出一场的满分是一百块大洋,他的全堂场面以及两个跟包的,一个箱头上的师傅,一个检场,都算在他的脑门钱中,共计为30块大洋。成班后,谭富英的扶椿社立即在北京的吉祥、华乐、开明、长安、哈尔飞、广德、三庆、中和等各大戏园陆续亮相。正如谭小培的预料,票房收入稳定,观众热情高涨,表演日益娴熟。在北京各戏园子演出了一个周期后,又陆续到天津、汉口、上海等地演出。当然演出的班底也在不断的变化中,仅旦角就先后更换了程玉菁、筱翠花、新艳秋、章遏云、陈丽芳、张君秋、梁小鸾等。
1941年,扶椿社的社长陈椿龄因病辞职,谭小培延请北京“三义永盔头社”的老板韩佩亭担任社长,请乔玉林先生担任大管事,同时启用当年谭鑫培班社的名字“同庆社”为谭富英班社的命名,外出时就学习梅兰芳的方式使用“谭富英剧团”的名义。这就意味着谭富英已经承袭了祖父的艺术衣钵。
就在谭富英37岁那年,他吸上了大烟,心灰意懒,每天再不想练功调嗓,演出《定军山》时,拿起大刀,也感到特别沉重,虽然外界还没有什么反映,但是自己已经感到身体的虚弱和精神的颓废。1946年,他便毅然决定自己一边戒烟,一边加紧练功。他特意请来一位师兄,每天在家中对他监督和陪练,练了八个多月,都没有演出。再演出是为某省的水灾赈灾义演,戏码是《甘露寺》,成绩很不错,从此他就彻底戒除了这个嗜好。
同庆社的名字从1941年起,一直使用到1949年。1944年,韩佩亭社长病故,谭小培又延请华乐戏园经理万子和担任社长。新中国成立后,裘盛戎亲自到大外廊营一号谭宅,以后生晚辈的姿态恳请与谭富英合作。从此谭富英的同庆社与裘盛戎的“戎社”合并,组建了“太平京剧团”。由梁小鸾为三牌旦角、谭富英的妹夫杨盛春为四牌武生、丑角为马富禄。为展示剧团的新面貌,他们首先排演了新戏《将相和》,在上海连续演出了40多场,轰动一时。不久,又到兰州为庆祝“天兰铁路通车典礼”演出了半个多月。回到北京后,根据政府的要求,太平剧团改名为北京京剧二团。1956年,从香港回到北京的马连良组建的马连良剧团又与二团合并,组建了北京京剧团。1957年,又与张君秋的北京京剧三团合并,1960年与赵燕侠的“燕鸣京剧团”合并,组成了北京京剧团。
从与裘盛戎、梁小鸾合作开始,谭富英先生就表现出一位忠厚长者的风范,但又不以长辈的身份压人。裘盛戎先生年轻气盛,在舞台上总有咄咄逼人之势,谭先生从不放在心上,虽然他的嗓音也是宽窄高低运用自如,扮相儒雅俊俏,堪称“最标准的老生奇才”,但是面对比自己晚出道的师侄,总是尽可能地突出对方。在与马连良先生合作时,他又以师弟的姿态,处处谦让,不管排演什么戏,他总是说:“我听师哥的。”总是把大轴戏让给马连良先生。例如马连良先生要与他合作《十道本》,他不会这出戏,完全可以不演,但是他丝毫没有犹豫,马上跟马先生说:“三哥,这出您得教我。”当天就到西单的马宅,毕恭毕敬地请马先生给他说戏。后来排演《赵氏孤儿》,马先生的程婴,谭先生的赵盾,这明明是一个费力不讨好的角色,但是为了增加前半出戏的分量,他主动到马宅,请马先生给他说关外唐韵笙先生演出《闹朝扑犬》的戏路,认真研究“花园”一场的唱腔,把一个不讨好的配角演得有声有色。就是平时走路、开会,他总是谦恭地礼让马先生,人们经常看到,谭先生让马先生先行,马先生请谭先生先行,最后是马先生挽住谭先生的手,并肩而行的感人场面。赵燕侠更是后生晚辈,参加北京京剧团是最晚,最年轻的一个副团长,为了不使她感到新剧团的“欺生”,谭富英甚至在她主演的《辛安驿》前面垫一出中型剧目《摘缨会》。所以说,北京京剧团那么多高级的艺术家在一起合作,却能够互相谦让,彼此和睦,与谭富英先生牺牲自己的名利,以身作则,顾全大局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所以裘盛戎先生在谭富英先生患病时,主动提出与他的师弟谭元寿合演《将相和》;赵燕侠在“文革”后也提出与谭元寿联合搞一个改革实验的剧团。就是在全国京剧名家演出大合作的《赤壁之战》时,他这个“活鲁肃”竟然主动把鲁肃这个角色让给李少春,自己演一个戏份不多的刘备。
谭富英先生是一位大孝子,早出晚归都要到父亲的房间请安,如果外面有饭局,遇到他父亲爱吃的东西,或者是什么新鲜的佳肴,他总是到帐房单交一份钱,请厨房再做一份,饭后用手帕包起来,给父亲送到当面,请父亲品尝。可是当祖国需要他到朝鲜战场慰问志愿军的时候,他的父亲已经卧床不起,病入膏肓了。他每天在床前伺候,却不敢说自己要到朝鲜慰问的事情。因为他明白,他是父亲唯一的儿子,在父亲临终时,父亲最需要的就是他。后来还是谭小培从别人那里知道了儿子即将赴朝的事情,主动对儿子说:“豫升啊,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尽忠不能尽孝,赴朝事大,不能耽搁,不要管我的病,我会好的,你只管去吧。”他这个大孝子听到父亲如此深明大义,感动得泪眼模糊,一再请父亲原谅儿子的不孝。他就这样毅然诀别了弥留之际的父亲踏上了征程。可是列车刚刚开到天津,就接到父亲逝世的噩耗。按谭家的规矩和他自己的心愿,他应该入殓、接三、出殡,大办丧事。可是当领导允许他回家奔丧时,虽然没有提出任何要求,同行们却都认为他这一回北京,是不可能再跨过鸭绿江了。因为按北京的民俗,父亲过世属于大丧事,必须戴重孝,最少也要守孝“五七”,而他,回到北京,哭别了父亲,将遗体刚刚入殓,就戴着热孝日夜兼程赶赴丹东,与慰问团的同志们一同跨过鸭绿江,深入到抗美援朝的前线战壕、掩体中冒着生命危险和零下20度的严寒在冰天雪地的露天广场进行演出活动。
在20世纪50年代末,剧团要到条件相对困难的唐山定期演出,他每次都主动请缨,作为德高望重的老艺术家和年轻人一样去完成最艰苦的演出任务。
正是由于马、谭、张、裘、赵五大头牌精诚合作,技艺超群,北京京剧团连续多年好戏不断,《赵氏孤儿》、《官渡之战》、《状元媒》、《三顾茅庐》等新戏层出不穷。在这些新排剧目中,从表演到唱腔,从音乐到服装、道具,进行了全面改革,使舞台演出焕然一新。不但不要国家负担工资等费用,每年还向国家上缴26万元,这按当年平均工资30元来说,无疑是一笔巨款。
谭富英的嗓音清亮甜脆,吐字行腔不过分雕琢,不追求花哨,用气充实,行腔一气呵成,听来情绪饱满,痛快淋漓,他的演唱被人们称为“新谭派”。因谭在幼年学过武生,故其在武功和身段动作上颇为灵巧、利索。例如他演出的《定军山》一剧,不仅唱工惊人,他那稳练的靠功和刀花动作,干净利落,引入入胜,把一个老当益壮的黄忠形象,演得活龙活现。由于他在艺术上唱做兼能,文武具备,是继马连良之后,成就显著,舞台生涯最长的“四大须生”之一。擅长剧目有《失空斩》、《战太平》、《定军山》、《桑园寄子》、《奇冤报》、《击鼓骂曹》、《洪羊洞》、《搜孤救孤》、《四郎探母》、《桑园会》、《珠帘寨》、《打棍出箱》、《御碑亭》、《群英会》等。
1959年,谭富英先生加入中国共产党。“文革”中,竟被江青等人勒令退党,遭受政治迫害。1977年,“文革”结束,谭富英先生恢复了党籍,落实了政策,本该心情舒畅地重返舞台的时候,他却身染重病,不幸于3月22日逝世。谭富英先生逝世后,北京文艺界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来自全国各地的同行、弟子纷纷赶到北京瞻仰他的遗容,为他献花,为他送行。他的遗体火化后,按国家的最高礼遇,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1924年与宋洁贞(宋继亭之三姐)女士结婚,生育寿颐(元寿)、寿丰(韵寿)、寿永(喜寿)三子,在宋氏生喜寿时因患产后风不幸早逝。1936年谭富英续娶姜志昭(姜妙香之女)女士,生下三女凤云、凤霞、凤珠,一子寿昌。1947年,姜志昭夫人病逝。1948年谭富英续娶杨淑贤女士,生子寿康、小英。子寿颐、寿丰、寿永和寿昌在京剧界分别工文武老生、丑角、武生和场面。

出生:1906年10月15日,光绪三十二年(丙午)八月廿八日
逝世:1977年3月22日,农历丁巳年二月初三日
人物分类
京剧 生行演员
科班院校
富连成社 富字科 学生
声明:内容由网友分享,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侵犯权益请联系我们修改或删除。